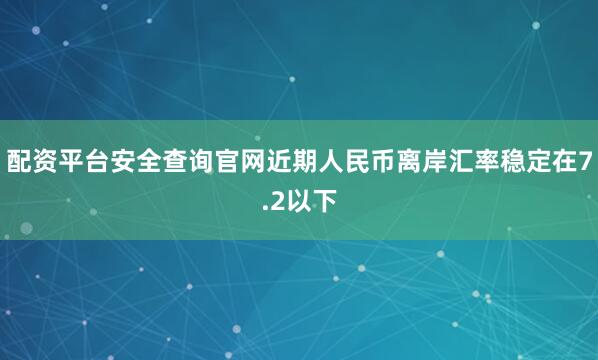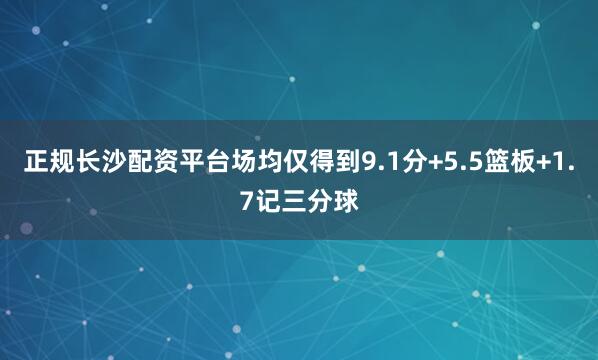文/潘彩霞(改写版)
1980年,漂泊在纽约的晏阳初用笔墨寄托乡愁,他写道:“我的故乡在四川巴中,那片土地上,留下了我多少脚印,踏遍了巴山的峰巅,行走过蜀水的岸边……”
他离开祖国,已整整三十年。
晏阳初生于1890年,家乡四川巴中,是家中排行第六的孩子。那天清晨,太阳刚刚升起,霞光满天,充满希望和生机。他的父亲见状,便给他取名“阳初”,寓意着初升的太阳。
父亲开设私塾,同时行医为人,言语温文尔雅,待人亲切,是个慈祥的长者。
与之相对,母亲则极为严厉,出身于大家族,持家有方,教子甚严,从不姑息溺爱。
展开剩余87%童年时代,晏阳初总穿着一身朴素的土布衣,尽管简陋,却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母亲时刻在身边叮嘱:“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,走有走相,吃有吃相!”
有一次,他在街上走着,忽然下起了雨,想到母亲严令不可奔跑,他只好冒着雨淋淋地,斯文地慢慢走回家。
还有两件往事令晏阳初心刻骨铭心。
其一是大哥酒醉后言语失态,被母亲严厉斥责。母亲召集全家训斥大哥,让他伏在一条长凳上,一边挥鞭,一边声音哽咽地说:“今天我不打你,是对不起晏家。小辈们怎能学你这般喝醉!”那时,大哥已婚,有妻儿。
其二发生在他六岁时。放学路上,他被庙里热闹的唱戏吸引,挤进庙内全神贯注地观看。忽然被背后推搡,险些跌倒。回头一看,是一位小伙伴,脸上洋溢着恶作剧后的得意神色。
晏阳初气愤不已,抬手给了对方一巴掌,留下一道清晰的五指印。小伙伴嚎啕大哭,晏阳初既愧疚又难受。
当晚,他迟迟不敢回家,最终还是免不了母亲的竹鞭惩罚。午夜时分,他被疼痛惊醒,发现母亲正含泪为他细心擦药。
母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做错事,就得承担责任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这句话,深深刻印在晏阳初心头。
数十年后,他在《九十自述》中写道:“这件事时时提醒我,要学会忍耐,忍耐,再忍耐!每当想发脾气时,只要想起母亲的竹鞭,我就会默念‘小不忍则乱大谋’。”
13岁那年,母亲的支持让晏阳初远赴数百里外的教会学校求学。那一路崎岖,山路陡峭,沟壑纵横,时有土匪出没,全靠双脚跋涉。
在一位传教士的资助下,1913年,他进入香港大学,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新生状元,获得一份皇家奖学金。
然而,这份奖学金附带条件,要求必须加入英国国籍。
晏阳初感到极度失望,难以想象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竟如此狭隘。
他满腔爱国热情,坚决对校长说:“我很穷,也很需要这笔钱,但我郑重地告诉您,这份奖学金我不要了!”
想到母亲的严厉,他默默忍耐。国家软弱,百姓受辱,他选择了当时少有人问津的政治经济学,希望为救国出一份力。
在求学期间,他痛恨香港社会的阶级和贫富不公,渴望民主和平等。听闻美国耶鲁大学是最具民主精神的学府,他便决定远渡重洋。
1916年9月,怀揣着仅有的几十美元,晏阳初实现梦想,进入耶鲁大学半工半读。
那时,美国排华运动盛行,他愤慨之余查阅大量资料,写下题为《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正义公理》的演讲稿。
站上讲台,他慷慨激昂地说:“美国的民主,不过是少数人的民主……”
演讲引起轰动,他赢得众多优秀学子的钦佩,其中包括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的儿子。
在华人留学生中,他声望显赫,大家常聚在一位华人牧师家中,他出众的口才更是打动了牧师的女儿许雅丽。
许雅丽是中荷混血,心怀对父亲祖国的向往,聆听晏阳初的讲述,逐渐走进他的心间。
爱情的甜蜜还未享受,愤怒的消息接连传来。
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,近二十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,他们大多文盲,承担最苦最累的工作,且因语言不通常遭凌辱毒打。
同胞的苦难深深刺痛晏阳初心。1918年6月,耶鲁毕业次日,他即启程前往法国,志愿为中国劳工服务。
两年间,他与华工同吃同住,教他们识字,办报刊,从此明确了毕生志向:
“一不图官位,二不图财富,我愿将所有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的劳苦大众,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,无怨无悔。”
1920年,学成归国。许雅丽早已在上海体育学校任教,静候他归来。
换下西装皮鞋,穿起长衫草鞋,晏阳初踏上了考察全国的漫长旅途。
九年后重返故土,父亲已逝,母亲双目几近失明。
听闻他放弃外交部和大学邀请,决心服务平民,母亲鼓励他说:“忠孝难两全,你是做大事的人,安心去吧。”
离别那天,母亲神情平静,直到他身影消失,泪水才夺眶而出。
一年多时间,他踏遍十九个省份。归沪后,与许雅丽结为伴侣,风雨同舟。
婚后,晏阳初创办平教会,全力投入扫盲事业,亲自设计《平民千字课》教材,选择长沙为首个试验区。
在各界支持下,长沙识字班有条不紊地展开,不论车夫、学徒,家庭妇女或老者,均得以进入课堂。
有一天,一位高大身影、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走进一座古庙,站上讲台。
此人正是青年毛泽东。
受晏阳初精神感染,陶行知、蒋梦麟等名士纷纷加盟,扫盲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。
晏阳初凭借卓越口才和高尚人格,吸引越来越多高级知识分子投身平民教育运动。
北大校长蔡元培感叹:“照此发展,数十年内,祖国千千万万被愚昧黑暗笼罩的人民,必将成为知书达理的现代公民!”
母校耶鲁大学持续关注这位杰出校友,1928年授予他荣誉文学硕士学位,颁奖辞中称赞:“他对东方的贡献,或许胜过战后任何人。”
在美国,晏阳初积极演讲,拜访政界、商界领袖。昔日同窗洛克菲勒二世,不仅邀请他度假,还慷慨捐款支持其事业。
平民教育运动如火如荼时,晏阳初将目光投向乡村。
1929年秋,数位知识分子穿长衫戴眼镜,现身河北定县街头。告别舒适北平,他们带着家眷,踏入这片风沙漫天的贫瘠土地,决心为农民服务。
许雅丽携子团聚,穿粗布衣,住农家漏雨屋,用苞谷面做“晏氏咖啡”。
晏阳初广揽人才,“副刊大王”孙伏园,戏剧才子熊佛西,哈佛硕士陈志潜,教育博士翟菊农纷纷加盟。
短短两年,百余名海外归国博士、硕士,辞去高职,骑毛驴走乡村,成为黄土路上的奇景。
几年教育后,定县农民焕然一新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记述:“黄土之中,年轻农民用锄头写下‘扫除文盲’,旁边姑娘则写着‘为国家塑造新公民’。”
近二十年间,晏阳初凭坚守与信念,开启了基层民智。
1943年,他再次赴美募款,恰逢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于纽约举行,被评为“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伟人”,与爱因斯坦等人齐名。
抗战胜利后,他试图说服蒋介石加大乡村教育投入,因内战爆发而未果。
1949年,随国民政府赴台湾,指导乡村建设。壮志难酬,短暂停留后远赴美国。
随后,他的足迹遍及菲律宾、危地马拉、印度……在全球黑暗角落点燃明灯,被誉为“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”。
虽欣慰,也难免惆怅。三十余年间,无论走到哪儿,无论人民多么热情,他始终思念着祖国。
1985年,95岁的晏阳初终得回归故土。飞机一落地,他便泪流满面,哽咽难言。
1990年1月,他在美国圆满走完百年传奇人生。遗愿所系,部分骨灰漂洋过海,长眠故乡巴中。
赤诚之心,终于获得安宁。临终前,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:“愿我毕生致力的乡村改造,成为我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。”
这是一份沉甸甸、丰富而厚重的精神财富。
发布于:天津市永华证券-配资服务平台-线下配资平台-安全炒股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